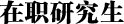李金華:把握中國數量經濟學發展的現實邏輯
來源:網絡
時間:2023-12-29 13:18:23
數量經濟學是中國學術界特有的學術名詞,它有別于計量經濟學或經濟計量學,但又與其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數量經濟學在中國發展非常迅速,應用十分廣泛。但數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是一條非均衡之路,應用研究發展很快,但理論方法發展緩慢,至今也未形成公認的學科范式;經濟計量模型廣受推崇,但應用實效不佳;中國數量經濟學需要從曲高和寡的境地走向更加“接地氣”的實際。
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非均衡推進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中國學者即開始探索使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活動和經濟現象。1979年3月,一批著名學者發起成立了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的前身-“全國數量經濟研究會”。次年6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賓夕法尼亞大學克萊因(Lawrence Klein)教授率賓夕法尼亞大學安藤(Albert Ando)教授、普林斯頓大學鄒至莊(Gregory C. Chow)教授、斯坦福大學安德森(T. W. Andersen)教授和劉遵義(Lawrence J. Lau)教授、紐約城市大學粟慶雄(Vincent Su)教授、南加州大學蕭政(Cheng Hsiao)教授,在北京頤和園舉辦了“經濟計量學講習班”,向中國學者傳授經濟計量學的理論、方法及應用。這便是在中國數量經濟學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頤和園講習班”。這次講習班后,以當時的華中工學院為先,一些高校開始講授經濟計量學、數理經濟學。隨后,中國學者也開始研究經濟計量理論方法以及應用問題,以經濟計量學為主體內容的數量經濟學始得在中國播種開花。
中國數量經濟學是按兩條主線發展的。一條是數量經濟學的理論方法研究,另一條是數量經濟學的應用研究。在經濟計量學傳入中國之初,早先面世的成果主要是教科書和譯著,此后陸續有專著面世,多是關于計量經濟學的經典。20世紀90年代以后,數量經濟理論方法成果日漸增多,研究走向縱深,成果的技術含量逐步提高,領域不斷擴大,研究也由淺入深、由點到面,方方面面多有涉獵,如概率模型設計問題、無限分布滯后模型、謬誤回歸、跨時橫截面的混合數據方法、數據缺失非隨機樣本問題、非線性經濟模型、虛擬變量回歸模型、回歸模型的函數形式、概率分布特征、聯立方程系統識別問題、時間序列的動態設定問題、貝葉斯推斷問題等,這類研究成果多以學術論文的形式出現,促進了高級經濟計量理論方法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中國數量經濟學發展的另一條主線是對現實問題的應用研究。這條主線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研究的對象多是特定時期社會重大問題、熱點焦點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一些學者用計量方法分析解決彼時中國的經濟,研究的領域多是各行業、各部門的問題。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10年后,經濟計量學作為經管類專業主干課程的地位在高校確立,這使得模型和方法在現實問題研究中的應用更加廣泛,如經濟全球化、可持續發展、經濟周期波動、社會福利成本、經濟轉型等。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數量經濟學的應用研究主題又有所變化,如全要素生產率、制造強國建設、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價值鏈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經濟高質量發展、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等。這些學術成果,多以模型為工具,以定量研究為主要特征,向精細化方向推進,學術味日漸濃厚。值得注意的一種動向是,國內應用性研究成果并沒有擺脫西方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的印記,一般均衡、總供給與總需求、價格粘性、彈性匯率、乘數原理、消費與儲蓄等概念范疇經常出現在數量經濟學論文中。
中國數量經濟學一方面在理論方法上豐富發展,另一方面也在向應用領域的廣度和深度推進。但兩條主線的發展是非均衡的。中國的經濟學者一直緊跟時代潮流,追蹤時代熱點,取得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而關于數量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卻滯后于應用研究。面對日新月異的經濟問題,數量經濟學理論有時很難給出答案,數量模型也拿不出破解之策。更大的缺憾是,數量經濟學的學科屬性至今仍無定論。一說是數量經濟學即計量經濟學;另一說是數量經濟學是規律性學科,有特定的研究對象;還有一說是數量經濟學并非學科只是一個學派。第一種觀點認為,國外只有econometrics(經濟計量學),而數量經濟學的英文名為quantitative economics。因此,數量經濟學也就是中國化的經濟計量學,是中國學者對經濟計量學的另一種叫法而已。第二種觀點認為,數量經濟學是一種融合多學科知識的方法論、交叉應用性學科,是龐大經濟學科體系的一個分支。第三種觀點認為,數量經濟學是經濟科學的一個學派、一個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一門學科。由于數量經濟學學科屬性的分歧,數量經濟學科的知識體系仍未形成定論。換言之,迄今還沒有邊界清晰的中國數量經濟學范式,學科的發展方向也呈多元化趨勢。更值得憂慮的是,數量經濟學至今沒有堪稱經典的、具有重大影響的教科書,也沒有系統深刻論述其學科范式的、權威的扛鼎著作。
模型崇拜與模型應用的失范
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數量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都有一種明顯的傾向,那就是模型崇拜。20世紀5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Kenneth Arrow)、蘇格蘭經濟學家布萊克(Duncan Black)等人就開始嘗試用數量模型來預測選舉、投票及利益集團的行為。如今,學界有一種普遍的認知:一切經濟學研究成果只要使用了模型,就貼上了科學的標簽,水平就是高的,結論就是可靠的。不單單是在經濟學領域,包括政治學、社會學領域,數量模型和方法都開始滲透。在當下的經濟學研究中,模型的應用已成為一種時尚,沒有模型就沒有了研究、就沒有了思考。這種觀點促使經濟學研究中各種實驗方法、理論模型、機器學習和軟件開發等應運而生,為數量模型的廣泛應用造成了推波助瀾之勢。一大批學者,尤其是海歸學者、青年學者都十分熱衷于使用數量模型進行各類經濟問題的分析。特別是經濟學論文的創作中,一些有影響的經管類期刊甚至都把是否有模型作為選稿用稿的重要準則。于是,經濟學領域眾多的新問題,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問題、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間產業轉移問題、推動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問題、數字普惠金融創新風險與監管問題、建設世界科技創新強國成效問題等,都成為當代學者們進行量化分析的對象。現在,數量模型已成為許多學者進行經濟學研究的首選法器,建模理論已成為數量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圭臬。
令人遺憾的是,對數量模型的崇拜或者迷信并沒有得到令人欣喜的回饋。經濟學研究中數量模型的設計及其對問題的分析,常常給不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展示應有的捕捉真實客觀世界的能力。當經濟學者運用各種數量模型煞有介事地進行經濟預測時,結果卻常常讓人大跌眼鏡。模型發現不了問題,發現了問題也給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該發生的問題依然發生,當問題已然發生并在向糟糕的方向惡化時,模型也不能給出阻止狀況惡化的高招妙策。運用數量模型,經濟學家無法預測出次貸危機的發生,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后,數量模型的推演也無法給出解決危機的辦法。全球性經濟危機時的經濟滯脹問題、新冠肺炎疫情下經濟的復蘇問題、建設制造強國的技術創新問題、各種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測度問題等,相關數量模型分析的結果都難說差強人意。大量的事實已經證明,感覺良好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精英模型已經捉襟見肘。
19世紀英國數學物理學家開爾文勛爵(Lord Kelvin)曾有過這樣一句話:“你能測量你所談論的事物并將它用數字表示時,你對它便是有所了解,當你不能測量它、不能將它用數字表達時,你的知識就是貧瘠的,不能讓人滿意的。”正是這句話成了許多數量模型追捧者的護身加持,促成了眾多經濟學者在經濟學研究中都刻意追求使用數量模型,而不論其是否合適或者是否必要。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曾針對這一現象說:經濟學家們過分熱衷于炫耀數學才華,這個群體忽視追求真相,樂于被光鮮的數學外衣迷得暈頭轉向。的確,數量經濟學理論和應用研究中,不少經濟學者樂此不疲地玩數學符號而漠視經濟現象的本質內涵,他們的學術研究脫離現實生活,陶醉于一個虛妄的、自以為美妙的經濟學邏輯怪圈,陷入一個由模型構成的公式化世界而不能自拔,而研究者渾然不覺,或者知曉但樂得其所。
現在,不少學者的數量研究程序往往不是先選擇問題,然后再依據問題選擇研究方法和搜集數據,而是根據研究方法和搜集到的數據來選擇研究問題。他們是為了模型和方法而研究,而不是為了發現和解決經濟問題而研究。他們追求成果形式,而漠視成果的內容。賓夕法尼亞大學斯羅德(Philip A. Schrodt)早已覺察到這種現象。他指出,定量研究已經故步自封,其在學術圈的傳播與蔓延已滋生了一種傲慢情緒,形成了一種定量霸權。由數量模型得出的結論,已被普遍地認為是一種科學的、完美的、毋庸置疑的高端真理。但事實上,大多數的模型測度和分析只是一種科學的表象,而非事物的本質和實際狀態。數量模型與現實世界的關聯性表現得并非淋漓盡致,而是模棱兩可。在復雜的經濟問題面前,經濟學家們無力用更加直接、易懂的語言來展現其所擅長的知識,揭示事物演化的規律。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只要建了模型,研究方法便有了充分的正當性,結論便有了合理性和科學性。事實上,經濟學者和經濟學家所設計的模型,相當多都是象牙塔里的產物,他們的結論有時就在假設中,他們使用的數據通常是經過一次或多次差分過,或一次或多次修勻過。那些數學符號、方程式里沒有產業結構的演進和全球市場的變化,也沒有技術創新和國家能力,只能淪為一些學術精英互相欣賞的“智力游戲”。
從曲高和寡到走向實際
數量經濟學自身在發展的過程中也暴露出諸多問題。一方面,理論方法少有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應用成果的科學性、精準性也得不到有效驗證。在經濟預測時的判斷失靈,對重大危機無計可施,常使得數量經濟學陷入難堪的境地。有學者認為,數量經濟學的發展現實與理想漸行漸遠,數量經濟學只有數量的增長,而少有質量的突破;數量經濟學遠離現實,缺少重大理論創新,看不出卓越貢獻。因此,數量經濟學需要走下神壇、回歸本原、貼近實際。
事實上,模型不是萬能的,也有刻畫不了的現象和分析不了的問題。所以,經濟學者不能迷信模型,也不能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無限延伸到社會科學;不能把腦袋中建構出來的那些虛無縹緲的藍圖當成社會的真實圖景,以為一切盡在自己的掌握中。那種一切經濟問題都可依靠模型來解決的定量霸權思維,把數學理論當作判定事實的決定性依據,混淆了客觀事實與數學推理,模糊了科學與偽科學的區別。
數量經濟學要發展,需要跳出科斯(Ronald Coase)所批評的“黑板經濟學”的窠臼。數量經濟理論不能停留于計算機上的模擬,止步于沙盤上的推演,也不能滿足于邏輯上的自圓其說和理性經濟人的心理預期。經濟科學的一切理論、方法只能來自于偉大實踐,能否準確回答和解決好現實問題是檢驗一切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科學性、有效性的根本準則。數量模型需要有哲學思維和人文情懷。模型所談論的合作應該是人的合作,而不是木頭的合作;模型所討論的競爭應該是人的競爭,而不是天使的競爭;模型所探討的博弈應該是以人作為主體的博弈,而不是計算機的博弈。數量經濟學理論方法的發展必須有超強的刻畫真實世界的能力,必須能直面真實世界的復雜和挑戰,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敢于回答和解決重大現實問題。這是當前和未來較長一段時期數量經濟學知識體系或學科范式建設不能回避的重大責任。
數量經濟學的應用,要扎根于實踐,始終以推動人類進步和經濟發展為目標,解決實際問題,體現科學精神,為人類創造福祉。應用研究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經濟學理論方法的發展要契合中國發展實踐,服務中國經濟增長,真正把經濟學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這是中國數量經濟學肩負的歷史使命和重要任務。199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集體)-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曾通過了一個《維也納宣言》。宣言聲明:世界各國的科學家都有責任,通過讓民眾廣泛知曉由自然科學之史無前例的增長所帶來的危險和提供的潛能,而在民眾教育方面作出貢獻。這顯示,科學家這一群體因為具有專門的知識,對于一個時代最緊迫的問題具有專門的本領,則順理成章地要肩負特別的社會責任。由是,數量經濟學的應用研究只有承載了社會責任和時代使命,才是真學問、大學問,才是真正的科學,才會有生命力。數量經濟學的一切研究必須求真求是,蘊含時代精神、充滿人文氣息;必須尊重客觀經濟事實,運用科學手段作出科學認知,進而得出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科學結論,自覺地維護正確的價值判斷和社會公眾利益。
數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必須充分依靠數據、挖掘數據。沒有數據,數量經濟學理論方法就成了空中樓閣;離開了數據,模型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經濟學分析中的數據主要有三類:截面數據、時間序列數據和面板數據,此外還有選擇性樣本數據、計數數據等。這些數據的挖掘和開發催生了數量經濟學的經典建模理論、參數求解方法和各種檢驗等,這也構成了數量經濟學科的核心知識。數據的可得性對于數量模型極其重要,在研究對象中哪些因素是內生的,哪些是外生的,哪些是前定的,哪些是限制性的,都有賴于數據導向路徑,只有數據充足、要件具備方可實現研究目標。因此,數量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數據處理技術,離不開統計技術、計算技術、信息技術的創新。在大數據時代和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背景下,數量經濟學者需要面對新要求、適應新環境,充分利用各類數據,提高經濟計量模型設計的科學性和應用的精準性。
科學研究永無止境,學科發展未有窮期。數量經濟學不但要自省現實的舛誤,還要突破歷史的局限;不但要承擔理性思考,還要展開勇敢的批判。唯有如此,數量經濟學才能更好地走向實際并服務社會。